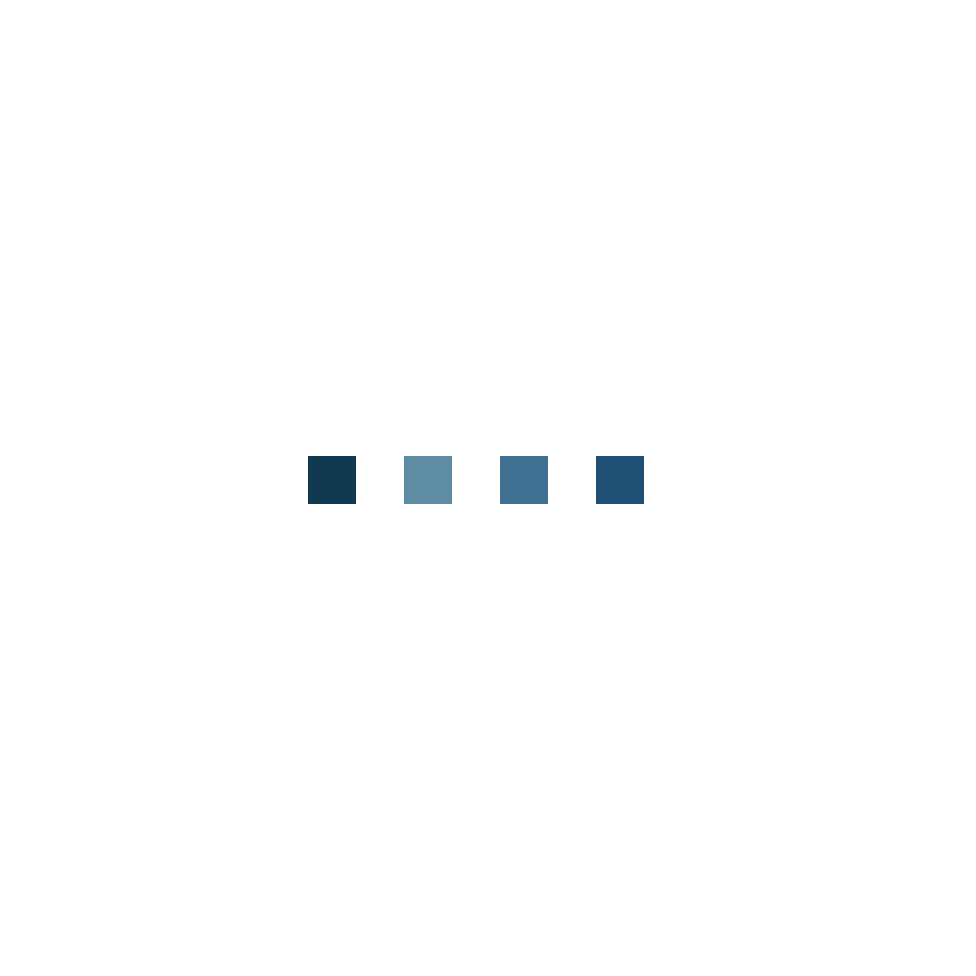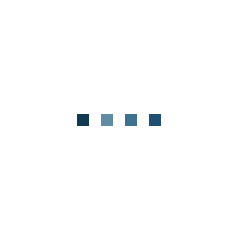這一年,元旦假期剛過,萬象更新,新新專程跑了一趟路去中國大使館辦台胞證,打算三月隨同日本學姐到北京大學探訪友人。使館裡講的雖然也是中文,可聽起來總多幾分拔高叫嚷。幾費周章拿到一本白皮證件,配色、材質都覺陌生。身心俱疲回到住處,才開房鎖,就聽到裡頭電話叮鈴鈴響。
「我要看看人生可不可以重來?」其明口吻難以分辨,既像玩笑,又像發恨。
他指的是結婚這件事,和別人結婚。「妳說聲不,我就把一切都停下來。」
這一兩年,再見其明,察覺他做事說話有幾分奇怪。問忙不忙?他說:「忙,忙,愈忙愈好。」問為什麼忙?他回答:「賺錢呀。」默默沒法再問答下去,他自己又加上幾句:「妳信也好,不信也好,現在,我把錢看得很重,咬牙切齒地賺,咬牙切齒地省。」
「賺那麼多錢做什麼?」她問過。
他看著她好一會兒,彷彿笑她依然幼稚,又彷彿咬牙切齒說出來:「讓妳後悔。」
結婚,卻煞有其事來通報,這是什麼意思?
她沒反駁,也不抵抗。走過從前,來到現在,她明白即使眼前並非她認識的其明,也不要試圖去尋找。現在的其明,穩定生活最重要,不要任意撩撥情緒,不要觸動愛情的盲目。是的,盲目,這話是其明說的,他老嘲諷別人的愛情,若非冷眼預料人家只是平庸地結了婚,要不就只能在不斷的拋棄與被拋棄中覺悟愛情的道理。她改問放假做些什麼?他毫無防備回答:「洗衣服,倒垃圾,給桌上萬年青換換水,要不,去同事家裡打點小牌。」
如此,便也過去了。結婚,卻煞有其事來通報,這是什麼意思?才說省錢,卻在國際電話叨叨絮絮講著單身怎樣延宕陞遷,長官怎樣給他介紹對象,就連舊同學都拉過線。「她和朋友投資有線電視,人脈夠,時代又來了,李文朗說別小看她。」「妳要知道,雖然上頭認定你是個人才,但考慮到你沒個家庭,總覺得不夠穩靠。」「如果當真樣樣好,為什麼不結婚呢?不會沒有原因的,妳要知道,他們若是沒辦法用正常邏輯來估算你的穩定度,你的企圖心,他們寧可拖著再看看,不放心把權力與責任交給你……」
她默默聽了很久。其明愈說愈沒勁,沒頭沒腦,丟一句:「妳看怎麼樣?」
怎麼樣?這一籮筐表面話,能怎麼接?她輕輕嘆口氣:「事情不能這樣處理。」
「那要怎樣處理!」平靜許久的其明突然爆炸:「我們處理多久了?哪一次處理,妳給過答案?妳的答案到底是什麼?」
來日幾年,台灣名號躍上國際新聞頭條這是第一次。
早春三月,台灣、中國兩地消息鬧得喧喧囂囂,她沒去北京,也沒回台北,日本學姊以為她預感靈通,殊不知只是因為其明使她意興闌珊。留在東京聽主播以憂心忡忡的語調報導,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引發台灣海峽情勢緊張,她既驚訝又茫然。來日幾年,台灣名號躍上國際新聞頭條這是第一次,所播出大陣仗的軍艦隊伍、砲火隆隆的畫面,也實在讓人分不清楚哪些是歷史剪接?哪些又是當下正在進行?
同樣海島,東京此刻正在迎接一年最美的季節。別人的國家,春櫻冬雪,一年去了還有新的一年會來,今年的美與和平會和去年一樣,理所當然。現在,這些理所當然與她劃開界線,熟悉的街道,和諧的景物,屬於他人世界,她自己的來處,灰濛濛的台灣海峽,黑水溝,過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現在戰雲密佈。
「我心裡很不安定。」台灣朋友淑瑤打電話來,說想一起吃吃飯,聊聊天。「也沒什麼特別事,就是悶,整天神經兮兮想哭,妳應該可以理解吧?」
她們約在常去的小店,吃天婦羅、草莓蛋糕,味道如常,卻沒法像往日吃得津津有味,淑瑤瑣瑣碎碎在抱怨日本男友淺野:「妳相信嗎?他居然跟我說:你們台灣人未免也太政治化了。」
學都不用學,躲都躲不掉,這才是政治化吧。
淺野從事中國研究,對亞洲現代史相當熟悉,一直很能理解照顧淑瑤的留學生活,不過,看來這陣子淑瑤的情緒不穩,連他也快消受不了。「不是我多麼懂政治,而是這些事情想來想去好喪氣,好無奈,一堵死牆,敲它沒用,繞道也不行,想著想著連論文、生活的困難都捲進來……」
「我懂,我懂。」她連說了兩次:「淺野的意思應該只是說,犯不著為政治陷入低潮,他希望妳開心……」
「開心?」淑瑤帶著氣怨,打斷她:「他關上電視,這事就沒了,輕輕鬆鬆就可以跳開,可是,我跳不開啊,我這麼難過,他卻說我政治化?」
她看著淑瑤的臉,她們彼此認識很久了。是的,與其說淑瑤是個政治化的人,不如說淑瑤對政治有潔癖,小小的恐懼,難怪她對被指稱為「政治化」那麼生氣。然而,學都不用學,躲都躲不掉,這才是政治化吧。
她想起前幾天,專教中國現代史的中島先生,以關心的口吻問:「你們這個第一次民選很熱鬧呀,說起來都是台灣人,李登輝和林洋港的差異,我可以明白,但是,李登輝與彭明敏,妳倒是跟我解釋解釋,不同點是在哪兒?」
她乍聽之下不明白中島先生的問題,但遲疑幾秒,又覺他問對了核心。原來街頭巷尾台灣人心知肚明、無奈接受的政治現狀,對外人而言,卻是霧裡看花。
「那是表與裡的差異。」她用了兩個日語的慣用詞回答,以為這樣會讓事情好懂一點。
「妳的意思是,那只是策略與話術的不同?」
老鹽瞧見她,大步走過來說聲嗨。
她沒點頭,也沒搖頭。她不想把「無奈」直接代換成「策略與話術」。可是,這怎麼解釋呢?中島先生會以為她在鬧情緒吧?為什麼她只消動用生活經驗就明白的事物,在他人而言,卻是相互矛盾,沒有一致性也沒有連貫性?
「很費解呢。」中島先生的眉頭都皺起來了。
戰爭的陰影,徘徊在海島台灣的上空。當兩千一百萬台灣人民將首度完全依其自由意志來選擇國家元首的前夕,對岸的中國卻在台海陳列重兵,企圖以飛彈火砲恫嚇台灣人民,左右選舉結果……
那天回家之後,她與淑瑤的傳真機,分別吐出了這樣一份名為「民主、和平、衛台灣」的宣言。傳送的周君,是她們朋友間比較早開始使用電子郵件的人。原稿來自美國,希望世界各地台灣留學生都能於所在城市,發起集會,以行動表達訴求。
新科技跨越了地理限制,東京的活動地點在新宿,新新去了,淑瑤沒來。人比她預期要多一些,生手生腳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好幾個拿麥克風發號施令,穿梭調度人力的身影裡,她認出了老鹽,好久不見。
他一會兒冒雨在廣場幫忙綁掛白布條,一會兒雨停了又忙著卡喳卡喳拍照。休息空檔,老鹽瞧見她,大步走過來說聲嗨,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聽說妳要回去了?」
「嗯。」
「待會要不要留下來?跟大夥兒去吃飯,聊一聊,有前輩捐了一萬塊慰勞金。」
她搖頭:「你們去吧,我得回去打包。」
「沒想到緣分這麼短。我以為妳會來很久的。」老鹽張開雙手:「來,道別一下,誰知道下次見面什麼時候?」
老鹽的懷抱不是溫暖,但很結實。上次那場酒醉,他後來倒底怎麼走回去的,新新仍然不知道。這兒的日本規矩是再怎麼荒唐,酒後吐真言,第二天太陽出來,就別再提起。老鹽握握她的手,使上點力氣,再見了。
之後,事情進行得很快,美國航空母艦開到台灣海峽,中國態度變化,台灣總統如期選出,日本櫻花如期綻放,國際搬家公司運走她所有行李,飛機鑽進雲層,重力與時間都暫時消失了。
她從班長手中接過接力棒,開始加速。
她坐在教室裡,勤勉地寫字。
周遭氣氛浮躁,校慶一會兒就要開始了,好些女孩圍繞在教室後方畫海報剪彩條,嘰嘰喳喳,發表意見,附合說笑,音調聽起來都比平常還要再高一些。
她寫完了功課,走出教室,看見班上的謝彩文依然坐在酸果樹下背單字。她打從旁邊經過,看看謝彩文的黑裙子,疑惑她為什麼沒有換上體育服。
時間到了,操場逐漸聚攏學生、老師、家長,還有對校的男孩們,興致勃勃,熱熱鬧鬧。她們排好隊伍,隨著開幕樂聲魚貫進場,通過司令台,隊伍前端執旗的是副班長,她有定然不笑的本事,任憑掌聲一層一層如潮水漲高,不改其志。
接著是體操表演、射箭校隊展示、接力賽跑。她從班長手中接過接力棒,開始加速,計算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而,後方選手愈來愈追近她,眼看就要超過她。她繼續使勁,加油聲簇擁,然而,對方還是從她身邊追過,然後,愈拉愈遠,愈拉愈遠……
怎麼辦?心臟擂鼓似地跳,羞恥與絕望完全把她籠罩,怎麼辦?一整班的的榮譽,就從她這段跑程開始落後……
前方跑道即將轉彎,一念之間,她忽地旋身向右,偏離了跑道,校門口向來看管她們遲到的教官此刻應該也擠在哪兒看熱鬧吧?她使勁快跑,沿途人潮嘴巴一張一張打開,驚叫著,伸出手來,攔阻她,主持比賽的體育組長抓著麥克風大喊:捉住她!捉住她!
「人家是永遠的十七歲,而我們現在幾歲了?」
她倉皇醒來,口乾舌燥,覺得腳下激動尚未停止。昨夜因為頭疼吞了止痛藥睡,沒想跌入那麼久遠之前的記憶。
她走到客廳,地板濕濕冷冷直往腳心裡鑽。「怎麼不穿拖鞋?」臨玉招呼她:「趙偉等一下回來,妳要先吃點什麼嗎?」
「有沒有水?」她往廚房走:「黃昏睡覺老作夢,夢得我口乾舌躁。」
「夢什麼了?」臨玉遞給她一杯水,在餐桌上和她對坐下來。
「高中時代辦校慶。」
「不錯呀,青春夢。」
「還跑接力賽,累死我。」她喝光玻璃杯的水,想起什麼似的:「對了,妳記不記得我們班上一個叫做謝彩文的?」
「謝彩文?」臨玉想了一會兒:「升高三前死掉那個?」
「嗯,妳還記得她長什麼樣子嗎?」
「不記得。要有也只是一點點。妳怎麼忽然問起這個?」
「剛才夢裡我看見她。」
「那妳不就看見她長什麼樣子了,還問我。」
「我沒看見她的臉。」
「這事想起來還真久。」臨玉嘆口氣說:「人家是永遠的十七歲,而我們現在幾歲了?」
今天,我們相聚一堂,在廣大同胞的面前,以莊嚴歡欣的心情,舉行慶祝就職大會。今天,我們相聚一堂,在廣大同胞的面前,以莊嚴歡欣的心情,舉行慶祝就職大會。這個盛會,不僅是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副總統任期的開始,更是國家前途與民族命運嶄新的開端。今天,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正式邁進「主權在民」的新時代──
這班車從景美到東湖,兩個地名都很美。
新任民選總統正神情愉快進行演說,她盯著電視畫面,覺得有些隔閡,從下飛機以來,感覺不到過去幾個月這個島上的氣氛,而人們也不再談起。
臨玉走過來:「下午我要去作產檢,妳要不要陪我一起去?」
她沒聽見,她心裡在想其明為何要選在這一天舉行婚禮。五月二十日。一個未來的紀念日。嬌美妻子或將年年嬌嗔問其明道:你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兩個人婚姻,三個人紀念。何必呢。忘掉吧。
「要不要去嘛?」臨玉搖搖她的手臂,又問一次。
她關掉電視,扯個謊:「我要去找工作。」
公車駛入巷道,開到底,再掉個頭,反向發車過來,新新估計大約再等四、五分鐘便可上車。這班車從景美到東湖,兩個地名都很美。臨玉說從東湖上車的的同事喜歡取笑: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可惜流過這城的並非長江,而是開膛破肚的交通線,台北修路斷斷續續有十來年了,一會兒是鐵路地下化,一會兒是大眾捷運,過幾年,又蓋了好幾條外環快速道路,種種基礎建設都是遲到的,因而,不管哪個點挖下去,都是高密度、高流量、高成本,那些年,大家的上下班時間都特別長,約會遲到都有了理由,計程車就算載著客人也是怨聲連連。
陣痛期。轉型期。不得不。新新記得那些年常常聽到這類說詞,人們在黑暗中等待,靠著經濟泡沫、飆升的房地產,安撫自己的心。離開幾年,再見台北,新新感覺到有些手術已經完畢,這座城市露出新的肌理,就連她離開時被拆得光禿禿、坑坑洞洞的七號公園,也長出了微薄的綠意。
台北風景,再怎麼陌生,如今也看熟了。
車過森林公園,新新拉鈴下車,依地址去找約好要看的租屋。她想回到熟悉的區域,不過,租屋空間不如預期,更糟的是頂樓加蓋。頂樓加蓋說起來也沒什麼,可是,當房東領著她從四樓樓梯再往上爬的時候,她忽地明白過來,她太熟了,大學朋友十之七八都住在這樣的空間裡,光憑樓梯、門板,她也立刻可以回想起來,那些被隔閡與被排除的感覺,雖說當時頗能自得其樂,自由自在,不過,時移事往——她愈往上爬愈起了情緒——為什麼房東不事先告知呢?
她沿著來程走回去,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的天橋,是剛上台北來時所記得的第一個地標,如今它舊了,掉色了,走的人也少了。她一階一階爬上去,走到路面正中央,停下來,龐大而兇猛的車流,和多年前一模一樣,彷彿從胸口穿過,滂沱而來,又快速流去。四面八方的喧鬧,台北風景,再怎麼陌生,如今也看熟了。她未必想做個台北人,可再回到這座城市,她要與它保持什麼關係呢?那些寄生、淘金、把人生往上爬、向前走的幻想,全都賭注於台北的種種故事,在連續劇裡、在流行歌曲裡,都演過了、唱過了,但,那會是她的故事嗎?
她並不打算在臨玉家借住太久,儘管他們剛買了房,很樂意新新一起分擔。房子離外環快速道路不遠,未來捷運景美新店線也預計通過,趙偉是把這些都搞清楚,才把台中家裡的一筆積蓄拿來墊了頭款。曾信誓旦旦不留台北的臨玉,現在,菜哪兒買,垃圾車什麼時間來,清清楚楚,冰箱上旅遊買回來的風景磁鐵,壓著營養食譜、社區活動、仙跡岩地圖,好貴一雙健走鞋也捨得買,她痛改前非地朝新新說:「以前穿鞋都買小了,搞得現在拇趾外翻,痛啊。」
車廂內是明亮的,人是靜默的。
她打開媽媽手冊,把其中一張黑烏烏的圖指給新新看:「看到沒?這個白白的點就是心臟。還有,妳看出來沒?這是手,這是腳。」
「是嗎?真神奇。」新新看得糊塗。
「當然神奇。臨玉語氣裡有埋怨又有喜悅分享:「誰叫妳不陪我去產檢,如果妳聽到那個小小的心跳,碰、碰、碰,包妳腦袋空白,眼淚掉下來。」
臨玉曾經沮喪,也曾經疏遠,可漸漸她恢復了青春時期照顧新新的習慣,強勢,慷慨,見過世面。她的情緒依然濃烈,但論到家庭,脾氣便轉成了耐磨,撐傘似地護衛所愛的人。新新難免驚奇:感情真能這樣收服一個人?那個三不五時跟教官吵架,連退學也不怕的臨玉,現在懂得讓步,以退為進,說些違心之論也是可以的。以前是她問臨玉:「接下來,妳打算怎樣?」,現在改換臨玉催促她打算現實。
「妳為什麼不告訴他,妳要回來?」臨玉指的是其明的事。「妳回來,問題不都解決了嗎?」
她搖頭。她想說,事情不是這麼簡單。但又有多複雜呢?
在臨玉家住過一個夏季,接連來了幾個颱風,台北縣市到處淹水,她從電視新聞裡學了世說新語:土石流。秋天,她遷到木柵,從公車客轉成捷運族,萬芳醫院上車,無人駕駛的車廂,玩具似地轉過一個彎角,進山洞,出山洞,兩三分鐘,便穿過了原本阻絕、多墳亂葬的福州山。
在那兩三分鐘內,車廂內是明亮的,人是靜默的,她偶而會想起一些事。比如說,以前搭別人的摩托車經過殯儀館和辛亥隧道的感覺;比如說,母親,那麼害怕死亡;比如說,父親,不知多少人的父親含冤葬在這座山裡。
這是個唱歌好聽的人呢,她忽然想起來。
在台北的景觀裡,這條軌道彷彿橫空移植,使她錯覺時間倒著走回了東京,而非未來。可這班列車,在台北,確實是指向未來的,乘客新鮮又帶著緊張,要等到列車穿出了六張犁,進入市區,人們的神色才恢復正常,銀行,學校,餐廳,服飾店,一個急轉彎,來到復興南路,木棉花,發黃的舊公寓,跟捷運軌道差不多的三樓高度,有扇窗戶往外掛了看板,上面寫著:學唱歌。
唱歌怎麼學呢?看板顏色、字體有些舊日遺緒,不知掛在那兒多久了。唱歌,勾起新新很久以前中學校園裡的記憶,每天早晨,一兩個早到的音樂班學生,在活動中心的長廊,反覆吹著長笛,或許那就是他們的早自習吧。那段記憶裡,有謝彩文,有楊臨玉,還有她自己,各懷心事又安安靜靜背英語、寫測驗卷,聽著那些風中送來的音符,一天兩天聽熟了,經常是莫札特,斷斷續續,錯了音再重來一次。
可那也並非唱歌。唱歌怎麼學呢?世上有各式各樣的人,各式各樣的經驗與樂趣,她想,為人父母懷著明星夢領兒女去拜師學唱,莫非就是這般情景?也可能成年人在疲憊日常裡受了哪一個奇妙看板吸引,一念之間便走進哪棟公寓,推開門,學跳舞、學瑜珈,為什麼不能學唱歌呢?
浮想聯翩,列車如鳥在林間棲息,進站,下幾個人,又上來幾個人,其中一個經過她,又退回來,看著她。
啊。她不自主發出聲音。程立人。
這是個唱歌好聽的人呢,她忽然想起來。

「好久不見。」程立人微笑:「什麼時候回來的?」
(本文為部份節錄,完整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2017年7月號167期封面專輯‧賴香吟)
作者小傳―賴香吟
1969年生,台南市人,台大經濟系、東京大學總和文化研究科碩士。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台灣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九歌年度小說獎、台灣文學金典獎等。著有《文青之死》、《其後それから》、《史前生活》、《霧中風景》、《島》、《散步到他方》等書。新作《翻譯者》即將出版。